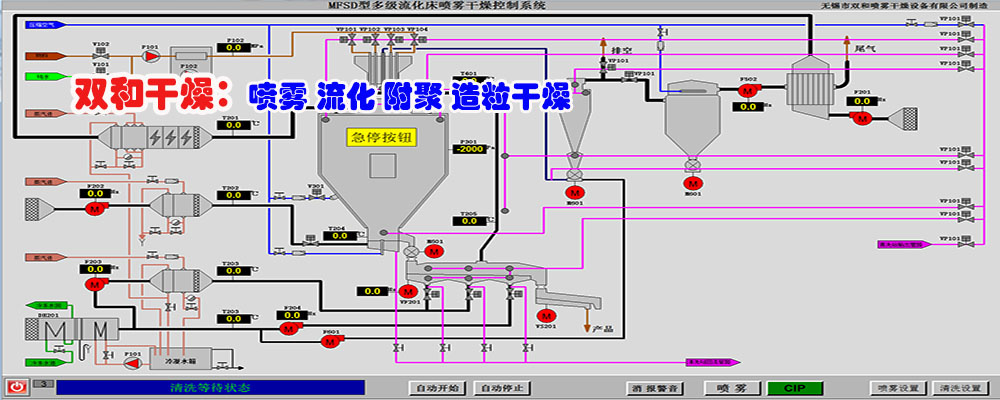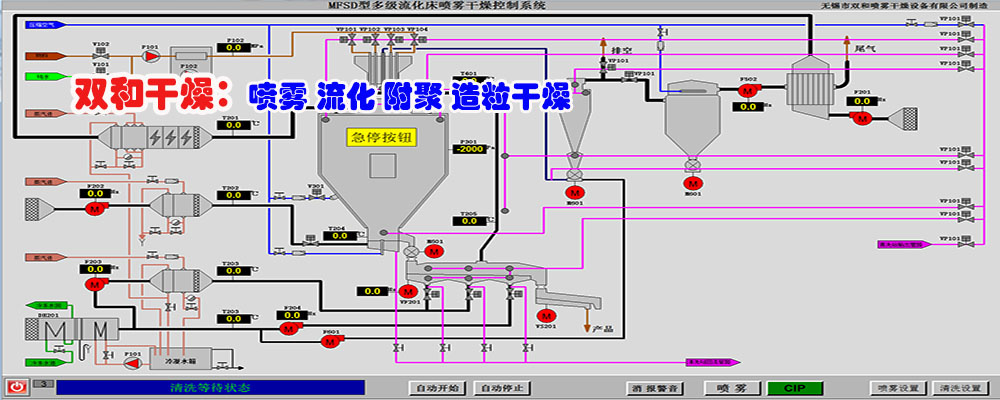|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那是一段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曠世之舉,那是值得我們用心記住的一段歷史。很多年以來,后人們通過各種文藝作品(包括電影、影視、演出等)對這段歷史進行弘揚與傳承,探索那些英雄們是以什么樣的信仰和什么樣的情懷,才能完成這這場艱苦卓絕的、驚天動地的偉大歷史篇章。
信報從今天開始推出《記住長征》特別報道,采訪文藝各界人士,請他們談談對長征的記憶以及長征精神對他們的影響。
作為國家級的藝術殿堂,國家大劇院今年以一部歌劇《長征》作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獻禮之作,首演時盛況空前,劇中所弘揚的“長征精神”讓觀眾備受鼓舞。信報記者日前采訪了作曲家印青,編劇鄒靜之,導演田沁鑫,指揮家呂嘉以及歌唱家閻維文,聽他們訴說如何用熱情和激情、用長征精神詮釋這部震撼人心的鴻篇巨制。
大劇院籌時最長的歌劇
事實上,國家大劇院早在2012年,便策劃將長征這一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歷史事件搬上歌劇的舞臺。《長征》是迄今為止大劇院籌備時間最長的一部中國原創歌劇,它以“信仰”和“理想”為創作關鍵詞,并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史詩的氣魄,一氣呵成地表現紅軍從瑞金出發,歷經湘江戰役、遵義會議、奪取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終會寧勝利會師等重要歷史事件。
為了探索長征題材新的表現方式,并能夠在劇作角度上有所創新,歌劇《長征》在充分尊重史實的基礎上,通過普通紅軍戰士閃爍著偉大人性光芒的感人事件,展現長征宏偉的歷史畫卷,忠實再現那段“苦難的輝煌”。
印青創作歷時4年4個月
音樂是一部歌劇的靈魂,經過仔細考量,院長陳平“四顧茅廬”誠邀作曲家印青為本劇譜曲。印青回憶說:“我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父母親都是軍人,打小就喜歡軍裝,除了是榮譽,更多的是責任、使命、擔當、憂國憂民等。最初接到任務我當時心里一熱,長征這是多么重大的題材,而且無論從藝術、思想性上去紀念革命先烈,還是從各個角度講都讓我心里怦然一動。一說長征就點燃了我內心的火。”
印青說,他為此重讀了許多長征的傳記、回憶錄,又重讀了收藏多年的四大本《中國工農紅軍歌曲選》,反復研究了劇本,“紅軍的文化是紅色的文化,而紅色文化源自于一個特殊的紅色基因,這個基因仍然是當下社會所需要和發揚光大的,那就是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這就是這部歌劇音樂中的靈魂。”
印青在創作中使用了十分廣泛的音樂元素,汲取了江西、貴州、陜北以及西藏等地民間音樂特色,力求真實且生動地再現紅軍長征途中的偉大行走。全劇曲譜經歷數次磨合推敲,于2016年5月正式完成,全部創作周期歷時4年4個月。
鄒靜之寫劇本用了兩年半
《長征》主創班底業界一流,劇本方面邀請到著名編劇鄒靜之執筆。
鄒靜之搜集并閱讀了大量的長征史料,將劇本中的每一字句精雕細琢,對主要角色彭政委、曾團長、平伢子等人物進行了深入而細膩的刻畫。劇本創作歷時兩年半,全劇既呈現出符合歌劇特征的抒情性,同時也再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歷盡艱難,但仍團結一致,保有不滅理想和偉大信念的堅強決心。
“當我讀過那一時期的《革命烈士家書》后,更為在那個時期的仁人志士,為理想英勇赴死的精神深深感動。為理想而生,為理想而死,這是那些人矢志不渝的信念。”鄒靜之說,“瑞金的三萬紅軍,到會師時只剩下7000人。意味著當年挑燈夜書的春閨夢里人,也多半成了兩萬五千里路上的無名骨。然而縱使面對著如此慘烈的犧牲,長征的隊伍也沒有散,戰士們的心也沒有動搖。是什么力量驅使著這支隊伍前進?其實就是夢想,是爆滿、充沛的正能量。”
田沁鑫:突出行走的力量
在劇作和音樂準確又富有時代感地表現長征精神的同時,為了能夠讓舞臺的呈現富有新意,導演田沁鑫與楊笑陽煞費苦心。田沁鑫表示:“我們希望通過《長征》突出行走的力量,展現紅軍戰士們困境中的突圍和精神上的輝煌。”
執棒該劇的指揮家呂嘉表示:“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都聽過長征組歌,看過大量長征題材的文藝作品。說實話,對于孩童時代的我來說,對長征里面振奮人心或是感人至深的故事并沒有產生與之相匹配的情感,反倒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經驗和經歷慢慢豐富起來,最近又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段歲月,感覺太了不起了。如果說藝術是一場長征的話,那么永無止境的藝術道路沒有終點和盡頭,只能活到老學到老。我現在應該還處于爬雪山和過草地的階段。我想我的長征就是追尋藝術的真理,永遠到不了目的地,這一生要做的努力就是盡可能地接近它。”
舞臺上,閻維文就是彭政委
在歌劇《長征》的排練中,閻維文也在長征精神的感召下,以軍人的堅毅,以對藝術的完美追求,挑戰著從業生涯中的第一部歌劇。“此前因為沒有合適的作品,所以,我從來沒有演過歌劇。但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一生中沒演過歌劇是件非常遺憾的事情。當國家大劇院邀請我演《長征》,并在劇中飾演彭政委這樣一個角色,讓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希望通過我們塑造的這些人物,讓觀眾感受到無論是我們今天的事業,還是未來的事業,都需要長征的精神、紅軍的精神,以及像紅軍戰士們那樣對理想和信念的執著。”閻維文說,觀眾在《長征》的舞臺上看到的是彭政委,而不是閻維文。
信報記者 張學軍
長征精神影響著我們
鄒靜之:縱使面對著如此慘烈的犧牲,長征的隊伍也沒有散,戰士們的心也沒有動搖。是什么力量驅使著這支隊伍前進?其實就是夢想,是爆滿、充沛的正能量。
印青:紅軍的文化是紅色的文化,而紅色文化源自于一個特殊的紅色基因,這個基因仍然是當下社會所需要和發揚光大的,那就是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
閻維文:無論是我們今天的事業,還是未來的事業,都需要長征精神、紅軍精神,以及像戰士們那樣對理想和信念的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