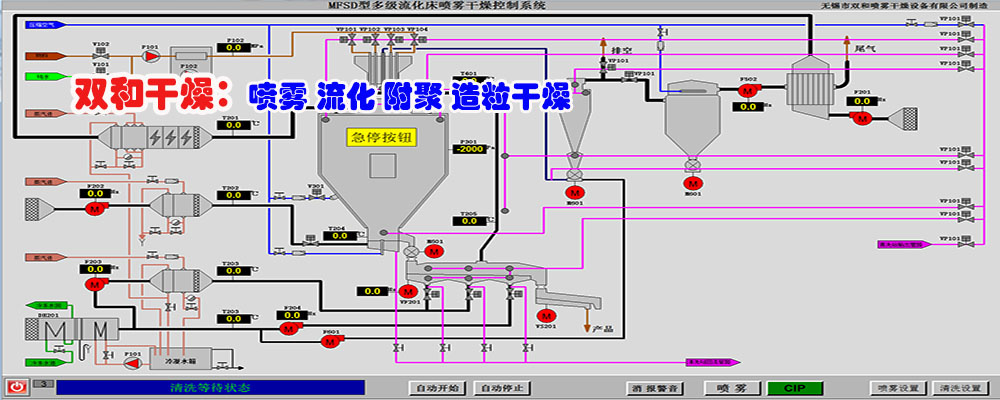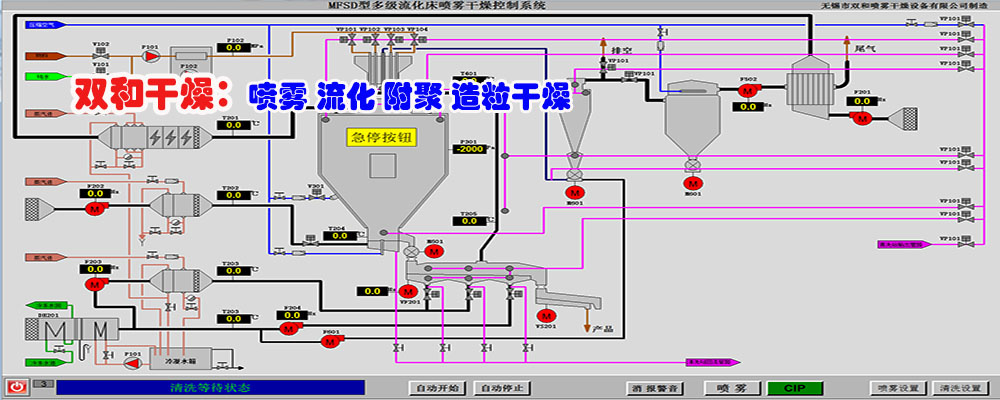|
關漢卿影響之深遠,一言即可蔽之。
我們常說自己“比竇娥還冤”,對于六月飛雪的典故也耳熟能詳——本是一年中最為酷熱的時節,竟爾天降鵝毛大雪,這樣的一幕可以說根植在了國人的心中,成為了千古奇冤的最佳代言。
如果能稍作考據,便會發現,“六月雪”的典故可追溯至戰國時期,當時效命于燕的鄒衍被誣入獄,天降大雪,燕惠王覺察到其中的冤屈,將這位名士釋放,漢代王充的 《論衡·感虛》中便寫道:“ 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
或許這樣的冤屈終能昭雪,這樁奇事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而關漢卿則將之引申,書寫入一部《感天動地竇娥冤》中,最終令這一典故街頭巷尾,婦孺皆知,以至于成為了中國文化語境的特殊組成部分,今人視之,亦嘖嘖稱奇。
關漢卿于我們而言,可以說既熟悉又陌生。
他以一幅畫像的姿態,出現在每個經歷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的課本上,甚至在臺灣的歷史教材上也能覓得蹤跡,以至于成為不少頑皮少年發揮主觀想象的素材——從這一方面而言,關漢卿也可以說成為了連結兩岸語境的共同話題之一。
可偏偏他生在了極力貶低知識分子的元代,在“九儒十丐”的社會背景下,這位戲劇家的一切又基本無史可考,時至今日,我們只能憑借《錄鬼簿》等戲曲專著中的零散記錄中窺得一個大概。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關漢卿是一個寫了《竇娥冤》的作家,僅此而已,然而,這位戲劇家所作出的貢獻,卻遠比常人所了解的要大。

(主頁君在這里再敲一次黑板,補充一點冷知識:這幅我們最為熟知的關漢卿畫像,是由畫家李斛作于1958年。)
附:李斛簡介
李斛(1919——1975),號柏風,四川省大竹縣人。著名中國畫家,美術教育家。
1946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精于素描人像,并嘗試作水墨寫生,徐悲鴻先生贊賞其“以中國紙墨用西洋畫法寫生,自中大藝術系遷蜀后始創之,李斛仁弟為其最成功者。”1948年應徐悲鴻先生之邀來到北平,在清華大學營建系任教,1952年轉至中央美術學院,1962年任中國畫系人物科主任。
李斛始終堅持于中西繪畫的結合,追求表現新時代精神和新題材的技法,在藝術和教學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他的人物畫《印度婦女》、《女民警》,革命歷史題材畫《廣州起義》和夜景山水畫《武漢長江大橋橋墩夜景》、《三峽夜航》等,均成為開創中國畫新領域的成功嘗試。1958年為紀念關漢卿戲劇創作七百年而完成的《關漢卿像》,我國和前蘇聯均選印為紀念郵票,成為新中國人物郵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畫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關漢卿是元代雜劇的奠基人,為中國戲曲的日后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他與白樸、馬致遠、鄭光祖并稱為“元曲四大家”,這一說法自元明一直延續至近代,得到了國學大師王國維等人的重新認可與強調。
他在當時的知名度,大概猶如今日之金庸,著作頗豐,代表作除了一部《竇娥冤》之外,至今流傳于世的尚有《救風塵》《望江亭》《魯齋郎》等,以當時的視角來看,他的作品取材多來自民間喜聞樂見的故事與事件,每當關漢卿的新戲上演,是時的觀劇場面也可以說是萬人空巷了。
話說回來,能在寶貴的歷史教材上占據一席之地的,又怎會沒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呢?一部《竇娥冤》的悲劇性早已得到了世界的公認,甚至有人將關漢卿冠以“東方的莎士比亞”之美譽,不過有一點還需要強調一下——關漢卿約生于金末,卒于元大德年間,而莎士比亞,則在200余年之后方才呱呱墜地。
(這一次的《關漢卿》中,王斑與于明加將分別飾演劇中的男女主角關漢卿與朱簾秀)
9月22日,我們將田漢先生編劇的一部《關漢卿》重新搬上舞臺,聊以為一點紀念——紀念中國古代戲曲文化的輝煌,紀念中國民族化戲劇的傳承,紀念北京人藝的誕生,也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這樣一位數百年前的劇作家,可能比多數人所能想到的更為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