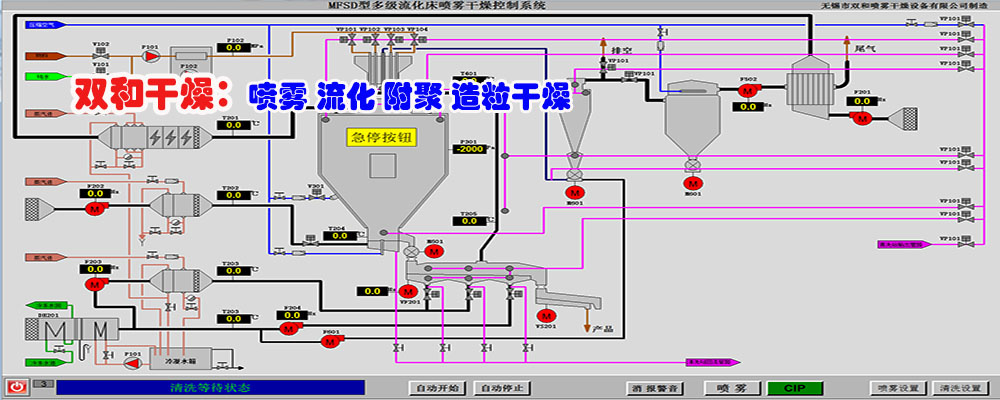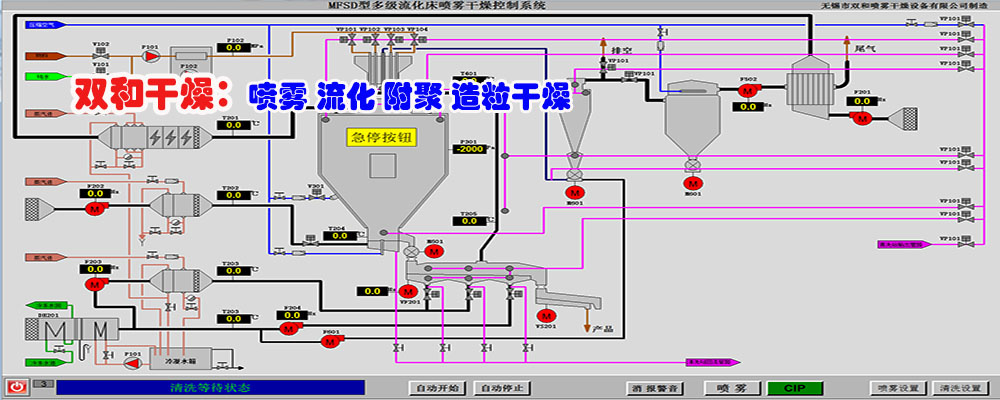|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全國普遍開展憶苦思甜教育,那時使用最多的詞句是“在那萬惡的舊社會”,控訴地主老財和不法資本家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罪惡。其實,萬惡的舊社會還包括往上朔被魯迅稱為“吃人”的幾千年封建社會,封建禮教亦是一條枷索,強迫女性纏足、家庭中奴役、欺辱媳婦等陋習,讓人也喘不過氣來,京劇《劉蘭芝》就是其中一部反映此狀況的形象作品,孔雀東南飛的名篇變成了形象的演繹,2017年6月2日梅花獎得主,宗張學梅的姜亦珊首次演出的此劇便獲得了戲迷的高度評價,一些觀眾紅了眼眶,心中悲憤,恨不得把惡婆婆揪下臺來,打罵一頓出出氣。其實,這位惡婆婆是封建禮教的代表而已,她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名丑梅慶陽把她演得十分刻薄無理,姜亦珊通過唱念做表把劉蘭芝的善良、賢淑,無限制的忍讓演到了極致,贏得了觀眾的高度同情,也使自己的表演藝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從劉蘭芝剛出場時的叫板“來了”,人們就可以聽出帶有憂郁的心情,表演上姜亦珊采用的是戰戰兢兢的身段和恐憂的眼神與表情,念白亦是輕聲細語。在娘家媽面前,亦珊唱出的詞“精誠致金石開霧散云消”,是對婆母充滿真誠與尊重的語氣,把這個“三從四德”觀念下的少婦純善的一面演繹出來。善卻被惡欺,歸婆家后又遭斥責,婆婆利聲“回來”,演員馬上以顫抖回應十分自然貼切。在“織絹”的重頭戲中,亦珊將“那焦郎他本是廬江小吏,每日里在公府常見相稀”,唱得情感充郁,滿宮滿調,不斷引來陣陣喝彩。“放燈”一段的表演更是精到,演員充分利用做表的藝術手段展示了“做媳婦實在難為”的窘境,手舉燈卻放在哪里都不行,都會遭遇利聲呵斥與挖苦貶損,驚嚇的表情,驚恐的眼神,足下的步,身上的抖,媳婦與婆婆在不大的空間里演繹“二人轉”,但絕不是插科打渾的東北民間表演,而是一種精神上的摧殘與凌辱。表演的逼真,二位演員的配合默契,讓人不由得深深進入劇情,替蘭芝抱屈鳴不平,既使焦母自討無趣的尷尬也讓無法使人大笑一場。這里姜亦珊在遞燈、接燈時的眼神與身段,行走時的水袖襯托、碎步,都在規定情境中讓主題得以充分的表露,也反映出演員扎實的功底。
其實,封建觀念的代表人物不只焦母一人,指望嫁妹發財的劉兄,強納妾的朱史,只知愚孝而順從母親的焦仲卿均在此列,從而引發劉、焦二人雖山盟海誓不嫁不娶卻無奈雙雙投水殉情的千古悲劇。
當然看此劇并非是批判封建觀念的活動,是欣賞藝術,看演員的表演是否能引人入戲。姜亦珊在后半出的“望官人切莫要灰心自棄”,唱出了對丈夫的一片深情,“耳聽得樵樓鼓催命三聲”表達了對強逼出嫁的抗爭,發出了“公道何在,理在何方”的質疑,唱得情感充沛,尤以拖腔引人入勝,觀眾席上掌聲四起。至投水一段,相愛卻橫遭拆散的二人決心以清流“沖洗數載的悲傷”,情至深處,觀眾在悲痛,喜悅和滿足的復雜心情中久久鼓掌叫好致意。這天,通州文化館滿坑滿谷,不少戲迷自南城、西郊、北郊趕來欣賞。紛紛稱贊演得太好了,重現了當年《白毛女》演出,有戰士欲開槍打臺上黃世仁扮演者的場景。姜亦珊常演的戲中人物多是金枝玉葉的郡主、公主,大氣端莊,但當她出演《打金枝》時,又顯露出了其喜劇才華,在悲劇《劉蘭芝》中飾演這樣一個人物,對她是第一次,又是首場公演,取得了圓滿成功,說明姜亦珊功底扎實,可塑造性強,不愧為劇院領軍人物,梅花獎得主,愿亦珊不斷高攀藝術高峰。再回到文頭的觀點,“一唱雄雞天下白”,封建社會奔潰了,當今欣賞這出戲,除了享受國粹藝術外,還為后來人肅清封建殘余,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貢獻了一力。

|